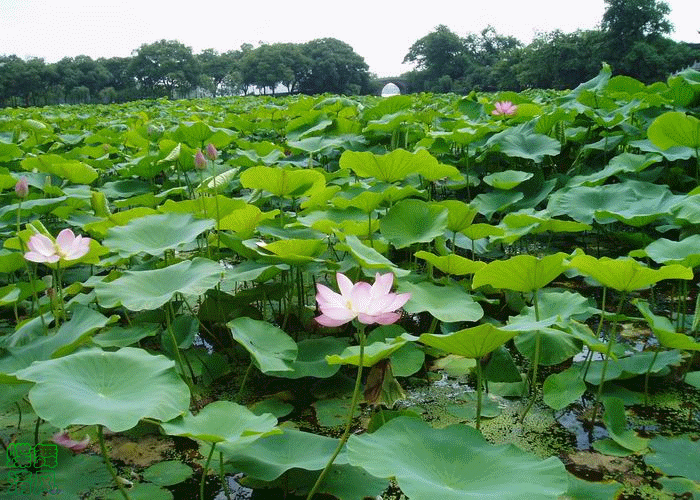内容提要:社区邻里关系的性质是城市社区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同时也是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社会基础。研究采取行动者主位的视角,基于社区邻里关系的广度、深度与自由度等三个维度,提炼出一个认识与分析我国城市社区邻里关系性质的理论框架,揭示了城市居民对社区邻里关系构建与社区参与的内生需求及其逻辑与机制。社区居民社会资本结构的不同、差序格局式信任结构以及对生活隐私与自由的追求,决定了社区参与动力的分化。社区参与呈现出“去精英化”、“老年化”以及“浅交往”式关系特征。因此,政府主导的社区建设应是居民自主的社会化机制的兜底和补充关系,而不应是以共同体为目标的社区全员式参与。
关键词:社区建设;共同体;社会资本;社区参与;自由
一、问题的提出
城市社区邻里关系性质的论争一直是社区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围绕着城市社会是否还可能存在地域性共同体的争论,西方学界内部存在社区消失论、社区保存论和社区解放论等三种不同观点(程玉申、周敏,1998)。社区消失论主张,在现代大城市社会中社会的一体化和生活的个体化,使得人们的社会联系受到地域的限制越来越小,不管是功能上的互助满足,还是心理和情感上的认同与归属,地域性邻里社区在人们的生活中都无足轻重(Stein, M.R.,1960)。而社区保存论则认为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并未带来社区的消亡,如赫伯特·甘斯(1962),桑德斯(1982)等,力图证明有相对明确地域界限、有凝聚力的邻里社区在现代都市中的继续存在。社区保存论者的观点也被学界批评其选择的田野调查社区大都是一些移民社区或者族群社区。而社区解放论主张在现代都市社会中,地域性共同体虽已式微,但并不意味着社会的解体,而是将人们从相对封闭狭隘的地域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在整个城市系统中形成“脱域的共同体”(Fisher,C.S.,1984;马丁·阿尔布劳,2001:252)。
自2000年社区建设运动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的性质在学界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由于我国社区的地理边界并不像欧美等国家那样是自然形成的,非由辖区居民投票决定,而是由政府基于行政区划管辖做出调整。那么,社区的地域范围在我国首先是一种行政区划边界,与欧美一些国家社区的内涵和边界并不同。相应地,关于我国社区性质的争论也具有独特性,大致而言主要存在三种路径:其一,国家政权建设论,认为社区建设过程中建构起来的社区不是一个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而是一个国家治理单元(杨敏,2007)。郭圣莉则进一步从建国后城市居委会的形成与发展史来说明社区的行政化趋势,社区实际上成为城市基层政权建设的一部分(郭圣莉,2006)。
其二,共同体培育论,认为共同体成为单位制解体后城市社会再组织化的基础,社区建设的目标要培育社区共同体(唐亚林、陈先书,2003;冯钢,2002)。通过积极的社区参与和密切的社会交往,构建社会支持网络与培育社会资本,被认为是共同体形成的关键(燕继荣,2010)。然而,社区建设在实践中却成了政府的“独角戏”,即政府积极推动,而居民的社区认同与社区参与严重不足,陷入“共同体困境”(陈友华、佴莉,2016)。对此,有的学者通过对居民参与的测量发现城市社区邻里之间的互动比较弱,形成的是“互不相关的邻里”(桂勇、黄荣贵,2006)。而有的学者进一步从社区文化建设(蓝宇蕴,2017)、引入社工组织构建公共空间(胡映芳,2017)、社区空间安排与人格化社会交往重建(熊易寒,2019)等不同角度,探索“共同体困境”的破解之道。
其三,社区复合体论。在对国家政权建设论和共同体培育论反思的基础上,近年来有些学者提出社区既非完全的行政单元,也非完全的共同体,而是一种“复合体”。刘建军(2016)认为“我国社区是国家治理与生活共同体的统一”。吴晓林(2019)认为“党建引领的政治逻辑、治理重心下移的行政逻辑、选择性参与的生活逻辑”相互交织,共同生产了社区复合体的形式。贺霞旭(2019)则从社区内部空间结构类型的差异分析对街邻关系的影响。不难看出,既有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学界已从不同维度认识与分析我国社区的性质,构成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然而,其不足之处是多采取宏观的结构分析视角,而缺乏从行动者的微观视角出发,分析作为主体的居民,对社区邻里关系与社区参与的内生需求及其深层成因与机制。
社区认同的基础是居民之间较为频繁的交往和互动,因为邻里不是既成的社会实体,而是一个不断建构的社会关系体(舒晓虎、陈伟东、罗朋飞,2013)。共同体式邻里关系具有广泛的熟人化互动、内在的信任与互助、外在的规范性约束等核心特征。由于我国城市社区是个相对的陌生人社会,社区参与被认为是形成邻里亲密互动与互惠式社会关系的前提与基础(杨敏,2005)。因为如果社区居民参与度低,邻里之间便无法形成密切的互动,自然也无法内生出信任、互惠关系、规范与认同。那么,在社区的地域边界之上,居民邻里之间能否发育形成亲密与互惠式社区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能否进一步内生出信任与社区性规范以约束居民行为,从而形成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这需要深入分析作为主体的居民对邻里关系构建与社区参与的内生动力。
基于共同体式邻里关系具有广泛的熟人化互动、内在的信任与互助、外在的规范性约束的核心特征,研究进一步提炼出社区邻里关系的广度、社区邻里关系的深度与社区邻里关系的自由度等三个维度,以行动者为分析单位,从居民主位视角理解我国城市社区邻里关系的性质及其内在逻辑与机制。本文素材主要源于笔者近年来在深圳、上海、佛山等多个城市的田野调查为一手资料,每次调查采取以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为主的质性研究方法,在对个案进行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再进行一般化的提炼。访谈对象包括街道办事处干部、社区两委干部、楼栋长、党员、积极分子和普通居民等多元群体类型。
二、社区关系的广度:个体的社会资本结构和社区参与
社区关系的广度是理解社区邻里关系性质的基础。在陌生化的城市社区,能否通过邻里关系的交往,以建设广泛的熟人化互动关系?这就需要从行动者的主位视角出发,理解居民对邻里关系建构与社区参与的内生动力。既有社区研究,虽强调地域性社区关系的重要性,但缺乏对居民社会交往关系的分类。基于对居民社会交往半径的观察,研究将居民的社会交往关系进一步细分为家庭关系、社区关系与社会关系[①],这些共同构成了一个人的社会资本总量[②]。对于不同的居民个体而言,不仅社会资本总量不同,而且社会资本的构成与分布也不同。由于个体时间和精力的有限性,家庭关系、社区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建构与维系具有潜在的竞争性,这就需要个体对不同关系的注意力分配进行权衡与取舍。当一个人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构成的社会资本存量愈充沛,那么其对社区关系构成的社会资本的依存度就会愈低。反之,当一个人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构成的社会资本存量愈匮乏,那么其对社区关系构成的社会资本的依存度就愈高。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经济收入水平越高、社会地位越高的居民群体,其由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构成的社会资本存量就愈充沛,通过家庭、市场和社会支持进行自我满足的能力就越强,对社区关系的依存度就比较低,因此通过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构建社区邻里关系的动力就不足。反之,亦然。
而从生命历程与家庭生命周期的视角去看的话,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与社区关系构成的社会资本结构对居民个体而言并不是一成不变,这也就直接影响到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居民对社区参与的内在动力。在人的生命历程中,不同的人生阶段与家庭的生命周期是相关联的,对于城市社区居民而言,结婚和退休是生命历程中的重要接点。下面我们以平均25岁成婚的年龄以及作为一代人的间隔,由此便可以将人生划分为四个阶段,将社区居民划分为大致四个年龄群体群体,即未成婚的青少年(0-25岁),已成婚的中青年(25岁-50岁),已退休的低龄老人(50岁-75岁),高龄老人(75岁以上)。城市社会结婚年龄在推迟,以平均25岁作为结婚的年龄是比较合适的。在我国退休时间未改革前,一般是女的50岁退休,男的60岁退休。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从生命历程的视角去观察,城市社区各个年龄群的社区参与度基本上呈现“U型曲线”,如图1。
图1:生命历程视角下社区参与U型曲线[③]
从图1可知,随着年龄的增长,居民对社区的参与度出现先降后升的趋势。结婚成家后到退休前的中青年对社区参与度是最低的,处于两端的青少年和老年人则对社区参与度相对较高。这也得到了很多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支撑,即社区居民参与呈现一种非正态分布特征,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经济收入高、社会地位高以及年富力强的中青年群体,社区参与度反而越低;反而是受教育程度低、经济收入低、社会地位低以及年龄大者,社区参与度反而越高(桂勇、黄荣贵,2008)。这与欧美等国家的社区参与呈现精英化的正态分布特征不尽相同。社区建设过程中面对以老人与小孩参与为主的困局,政府便致力于推动将社区建设的主力从老年人转向中青年群体,却始终无法有效动员中青年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和邻里交往。从主位分析的视角来看,社区建设将不得不面对社区参与呈现U型曲线的事实。
下面可以进一步结合个体的生命历程与社会资本结构的变化两个维度,来理解社区参与的U型曲线。社区参与的U型曲线显示,未成婚前的青少年阶段社区参与是不断降低的,然后经历了中青年阶段的低位保持,最后到老年阶段的回升和社区参与的复归。对处于结婚前的青少年阶段而言,从出生时起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交往的半径是不断扩大的,社会关系也就不断溢出社区的边界,社会关系相较于社区关系构成的社会资本就愈发重要。青少年对于社会关系的扩展主要是通过不同阶段的教育及其衍生出来的就业工作或其他关系。而对于已婚的中青年而言,不仅正处于劳动力生产阶段,而且上有老、下有小,具有繁重的家庭再生产压力,在闲暇和注意力分配上,则倾向于以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投入为主,对社区关系的需求度不高,因此社区参与动力也就不足。正如他们常挂在嘴边的理由为:“主要是没有时间参与。”
而到了退休的老年阶段,呈现的是老年人社区参与的回归趋势,主要是因为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逐渐后退,近距离的社区关系的重要性上升。这里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低龄老人和高龄老人。对于低龄老人而言,超出社区以外的各类社会关系尚能维持频繁的互动,及加上可能还要帮忙子女带孩子,因此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形成的社会资本存量能够满足情感、价值与功能支持等需要,还能维持超出社区的社会交往半径。但是随着子女单独买房立户和成为空巢老人,以及年龄的增长和身体行动的不便,老人日常能够独立出行的距离也在缩短,所以日益“遥远”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愈发不能满足需求,那么近距离的社区关系构建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那么,以行动者的主位视角来看,社区居民对邻里关系构建与社区参与具有能动性、选择性与非完全性,即不同的居民会结合个体的生命历程与社会资本结构的变化来选择性参与。
三、社区关系的深度:差序格局式信任结构与亲密关系
上一小节我们分析了社区关系的广度,社区参与呈现群体性分化。本小节则进一步去探讨社区关系的深度,即地域性社区邻里关系的互动能否形成亲密性互惠式社会关系网络。不同于村庄还是一个熟人社会,城市社区已是一个陌生人社会。那么,对于陌生人社区有无可能建设成为“疾病相扶、守望相助”的亲密性互惠共同体呢?其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形塑的深层次社会结构及其求助关系。在基督教文化的巨大影响下,西方社会形成了“个人-社会”的两极模式,且处于西方观念系统的核心,直接造成了“家”文化的缺失(杨笑思,2001)。为了保证个人对上帝的忠诚,基督教一方面贬斥亲缘性家庭的重要性,防止因个人对家庭的认同与归属而影响了对上帝的信仰,另一方面又树立起一种广义大家庭的信念,即所有教徒都平等相待、亲如兄弟姐妹,形成一种团体意识,以约束各种人际关系(安希孟,2005)。由此,形成了西方人重视团体生活,而轻视家庭生活的特征,个人及其自愿结成的社团在西方社会中至关重要,而家庭则隐没于“个人-社会”对立的两极之中,作用很小。这也是费孝通比较中西社会结构差异时,认为西方社会是“团体格局”,而中国则是“差序格局”的原因(费孝通,2013)。
与西方“个人-社会”两极模式下对“家文化”的轻视相反,“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中根基。如金耀基(1999:24)认为:“中国的‘家’是社会的核心,它是一个‘紧紧结合的团体’,并且是建构化了的,整个社会价值系统都经由家的‘育化’与‘社会化’作用以传递给个人。”梁漱溟(2005:72-73)认为:“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人们之间互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不同于西方“个人-社会”两极模式下形成“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我国则形成的是“个人-家庭-社会”三极模式下的基础社会结构。在“个人-家庭-社会”三维思维模式的影响下,形成了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式中国特色的信任结构。这种信任结构是以家庭为中心,以亲密程度为标准 ,将身边的人群自然而然的分成“自己人”和“外人”,并做出相应区分。随着亲密程度的降低,信任也随之递减(田毅鹏、刘杰,2008)。
亲密性互惠关系的建立和维系,核心在于求-助关系。而中国社会的求-助关系是嵌入在“差序格局”式的信任结构中的。在泛家庭主义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的求助关系不会发生在陌生人之间,讲究“礼尚往来”回报的中国人因为回报的不确定性,一般也不愿意接受陌生人的帮助。纵然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但是以“个人-家庭-社会”三极模式为基础形塑的“差序格局”式信任结构和求助关系并未根本改变。不管是城中村、老旧社区还是商品房社区居民,在发生重大困难或情感问题时,家人都是位于求助的第一梯队,其次则是亲戚和同学朋友,而这两类都属于可信任的“自己人关系”。陈福平和黎熙园对广州市城中村(村改居社区)、老城区和商品房社区三种类型社区,分别用随机抽样方式各抽取300位居民(除18岁以下、80岁以上者)作为问卷调查对象,回收有效问卷数分别为267、233和240,回收率为89%、78%和80%,问卷内容主要为个人的社会网分布,得到的社区数据调查结果验证了笔者的观点,如表1。
表1:不同类型社区社会支持网络关系构成(%)[④]
由表1可知,不管是在哪种类型的社区,家人都在个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关系中处于绝对核心角色,其次是亲戚和同学朋友关系。在城中村和老城区社区,相同的是在金钱需求和家庭重大事件两方面,个人向亲戚求助及给予支持的比例要高于同学朋友,而在情绪低落、婚姻与情感以及工作问题方面,个人向同学朋友求助及给予支持的比例要高于亲戚,因为同学朋友间建构的自己人关系,以亲密性的情感表达与心灵沟通为主,正所谓“知心人”。而对于商品房社区,同学朋友的关系在个人的社会支持网络中开始全面超越了亲戚的位置,仅次于家人的角色。对于城中村、老城区和商品房社区而言,一致的是家人、亲戚和同学朋友为个人最为重要的社会支持网络,而邻居的角色都无足轻重,几乎不发挥作用。那么,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区,数据为什么会呈现出趋同的结果?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个人的社会支持网络与社区关系网络的重叠度,即处于同一社区的社会支持网络成员的比例,如图2。
|
|
图2:处于同一社区的社会支持网络成员比例(%)
对于城中村社区而言,个人的社会支持关系网络与社区关系网络的重叠度高达70%以上,即一个人的家人、亲戚和同学朋友往往也是和他在同一个社区,也可以说是他的社区邻里,但是由于在填写问卷的时候,在身份重合时人们一般会选择填写其中最亲近的一个称谓。其次是老城区社区和商品房社区,社会支持关系网络和社区关系网络的重叠度依次降低。由此,我们看到社区邻里关系内含的变迁,即传统乡土社会下“疾病相扶、守望相助”的地缘邻里关系,不仅仅是地域性因素,更为本质的则是血缘关系在地缘关系上的投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底色。而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时代下的城市社区,则出现了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分离,社区邻里关系变成了一种纯粹地域性因素。当代地域性社区只是一个居民产生松散、疏离的社会互动的场所,而由于人们的利益空间、情感空间本身并不在地域性社区之中,因此当人们真正需要社会支持和帮助时,则要到地域性社区之外去寻找(陈福平、黎熙元,2008)。因此,我国“个人-家庭-社会”三极模式下形塑的“差序格局”式信任结构和求助关系,决定了在地域性的现代城市陌生人社区,居民并没有内生动力去构建亲密性社区关系网络。
四、社区关系的自由度:城市生活隐私的追求与共同体规范
前面从社区关系的广度和深度两个角度,分析了城市陌生人社区内邻里关系互动的低度性,可将之称为“浅交往”。通过密切的社会交往与互动,就能自动生产出互惠性规范和信任吗?在我国社会文化模式形塑的以“自己人”和“外人”为区分的社会交往信任结构下,社区陌生人关系自然属于不可信任的“外人”,“自己人”则是亲密性和支持性的社会关系。密切的社会交往与互动尚不一定能生产出共同体的社会性规范,更何况是在“浅交往”的社区关系中呢。而且,培育具有内生性社会规范的紧密型共同体,还将面临居民对现代社区关系自由度追求的矛盾,即居民对现代城市生活的隐私与自由的追求。因此,共同体式邻里关系建设便会遭遇社区居民的内生动力不足。
个体的隐私自由与集体性规范天然具有内在的冲突性,而集体性规范对于共同体秩序的生产又是必要基础。集体性规范往往是以公共舆论或闲话的方式为载体,对共同体内部的越轨行为或机会主义行为实施社会性惩罚和制裁,从而使得共同体内部的社会秩序得以可能。但是对位于城市生活的现代人而言,隐私是非常珍贵、不可缺少的。简·雅各布斯(2015:51-52)对此有精彩的观察与描述:“窗户里的隐私是世上能够得到的最简单的商品。你只要把窗帘放下来或调整百叶窗就行了。但是,将你的个人隐私限制在你自己选择的了解你的人之间,并对谁能占用你的时间以及在什么时候占用做出合理控制,这样的隐私在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是很稀有的商品,与窗户的朝向毫无关系。”
“如果仅仅是与你的邻居接触了一下就有被卷入他们的私生活中去的危险,或者,产生将他们纠缠到你的私生活中来的危险,如果你不能确定你邻居是什么样的人,那么合理的结果绝对是尽量避免对你的邻居表现出友好态度,或随便提供帮助” (简·雅各布斯,2015:57)。“由于一些非常复杂的原因,很多成年人要么根本不愿意与他们的邻居建立任何朋友的关系,要么如果他们因为某些社交的原因而必须这么做的话,他们只是把关系限制在一个或两个朋友间,到此为止,不再增加。各种各样确保自己受到保护的‘篱笆’在很多家庭里建立起来。害怕麻烦或心存怀疑使邻居间不再需要什么建议或帮助。为了保护剩下的最后一点隐私,他们不得不选择避免与他人建立密切的关系”(简·雅各布斯,2015:58-59)。城市生活中对隐私的珍视,实际上是一种不被外人恣意干涉的自由,是个人自主选择权的体现。而期望社区内部能够建立起密切互动、互惠式社会关系,是以居民之间彼此负有一定的义务和让渡部分隐私为基础,社区关系网络及其社会性规范犹如无形的“街道眼”,在时刻“监视”着居民的行为,个人的隐私与自由需求得不到保护。这也是政学两届希望通过动员居民参与而建立社区亲密互惠性社会关系,而却得不到作为被动员主体的居民的积极回应的内在机制。
案例1:上海市徐汇区GX小区的阮阿姨,今年62岁。曾经在小区里交了一个朋友,关系比较好,自己外出都会把家里钥匙交给她,帮忙照看。但是后来发现朋友因为嫉妒她,在背后说了她很多闲言碎语,就跟她绝交了。她不想再在社区内和居民交朋友,除了与之前交朋友的不愉快经历外,她说还因为和居民认识了之后,就会受到她们的关注,如果你穿着比较时髦的话,就容易遭到她们在背后评头论足和说闲话。[⑤]
在城市生活中,人们决意要护卫基本的隐私,而同时又希望能与周围的人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和相互帮助,而这两者之间存在一条无意识确定的令人惊奇的平衡线,划出了城市公共领域与个人隐私领域的区别。“而在这种平衡线内,人们就可以在公共领域内认识各种各样的人,而不会遭到不受欢迎的纠缠,不会产生厌烦,不会去找没有必要的借口、解释,不用害怕会冒犯别人,不会因要尊重别人强加的事务或承担诺言而尴尬,不会产生交往中常见的各种因承担责任而导致的连锁效应。一个人可以和另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处于一种良好的人行道上交往的关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可以发展为一种熟悉的、公共交往的关系”(简·雅各布斯,2015:54-55)。这样的关系之所以能够形成就是因为不知不觉中,它们给予了人们的公共交往一个正常的渠道。因为这种公共交往关系是发生在城市社区的公共空间,社区公共空间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特征,每个居民都可以自由平等的使用,也可以自由的进入和退出,就不会发生居民担心的被强加的交往关系,以及被迫卷入彼此的私人生活的风险。目前社区内大量存在的“点头之交”,也正是此类公共交往关系的体现。在社区公共活动空间,如街心花园、小广场、活动室等,老人、大人和小孩在社区内玩耍,常常有三三两两在一起自由的攀谈,像是比较亲近的朋友。事后问及,一般他们也都是出来在社区玩耍时,碰到了就聊几句,几乎不会私下里相互串门,进一步发展为私人关系。
案例2:佛山市禅城区SWZ街道HJ小区的陈姐,37岁,老家是东北的,性格开朗外向,喜欢聊天交朋友,在小区里算是善于交际的居民类型。居住的小区是一个房龄比较久的商品房小区,已经居住上十年了。她说邻居之间要居住七八年才能慢慢熟悉起来。陈姐说:“邻里之间都有戒心,不想让邻居知道太多,都有一种自我保护的心态。人都太复杂了,彼此之间无法知根知底。居住在一起十几年,仍然像个过路人一样。”她觉得社区内理想的交往关系为:“邻里之间关系融洽,但也要有隐私空间。互相之间能聊下盐有多咸,醋有多酸的生活,日常生活能有所照应就很好了。同时她也表示,对小区有没有真正的朋友也无所谓,老公的同学和朋友圈都在这里,经常一起聚会。[⑥]
即使像陈姐这样爱聊天交朋友的人,她对邻里之间的关系需求也是一种功能性的“浅交往”。实际上,在无意识中遵守了希望保卫隐私和与周围邻里接触与帮助之间的微妙的平衡线,这是通过无数个不经意的细小而敏感的互动细节确立的。在陈姐的个案中,即使在与她认为可以称得上一般朋友的2个邻居相处时,也不会去追问对方老公的名字,也仅仅知道彼此从事工作的行业,而不会追问对方的职位等更加私密性信息。在邻里关系融洽和家庭隐私空间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当然,对于不同的居民而言,这条平衡线的位置可能是不同的,由居民根据自己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和社区关系等多种因素进行权衡和相机选择。但是要想建设社区整体性的亲密互惠式社会关系,且具有内生公共规范、情感和价值认同与归属的共同体,是与现代城市生活需求相悖的,则必然会面临作为社区建设主体的居民参与的内生动力不足困境。
五、结论
城市社区邻里关系的性质是社区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同时也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社会基础,关涉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方向的精准定位。围绕着城市社区居民邻里之间能否发育形成共同体式关系的核心问题意识,通过采取行动者主位的视角,基于社区邻里关系的广度、深度与自由度等三个维度,研究发现社区全员式参与和共同体式关系构建与居民对现代城市社区生活的内生需求不相符。社区居民对邻里关系构建与社区参与具有能动性、选择性与非完全性,即不同的居民会结合个体的生命历程与社会资本结构的变化来选择性参与。从横向社会分化的视角来看,城市社区参与呈现为“去精英化”,和农村社区的“精英化参与”是相对的,具体表现为社区参与的非正态分布,越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经济收入水平越高和社会地位越高者,社区参与意愿与社区参与度越低。从纵向生命历程变迁的视角来看,城市社区参与呈现为“老年化”。而从我国社会“差序格局”式的信任结构、城市居民对生活隐私的保卫与社区邻里关系和谐之间的平衡动力上看,社区居民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属于一种非亲密性关系式的“浅交往”,理想状态是基于可自由进退的公共领域内的社区公共交往关系,经过持续的发育,也可能发展为一种相对比较熟悉的公共交往关系。因此,从社区居民交往与互动的内生动力去看,我国社区参与呈现出“去精英化”、“老年化”以及“浅交往”式的公共关系建构等特征。
从行动者的主位视角出发,理解社区居民对邻里关系构建与社区参与内生需求及其机制的理论化提炼,将对新时期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带来启示。单位制解体后,部分精英群体通过市场化和社会化机制实现再组织,如职业团体、趣缘团体或学缘团体等,因此便对社区机制的需求和社区参与动力不足。相对于社会化机制下参与者主要为生产者精英群体,社区机制下的主要参与者则呈现出“去精英化”、“老年化”的特征,可称为“剩余群体”,对社区邻里关系建构有需求,以及对社区建设有依赖。因此,政府负责的社区机制应是居民自主的社会化机制的兜底和补充关系,社区建设的目标与依靠主体则应该是对有内生需求的“剩余群体”的再组织,而不应是试图以共同体建设为目标的社区全员式参与。因此,从实践出发对城市社区建设目标与社会基础的重置,将有助于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创新的精准化,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的效能。
参考文献:
安希孟,2005:“家、国、同胞,与天下万民——中西哲人及基督教的家庭观”,《宗教学研究》,2005,1:91-95。
陈福平、黎熙元,2008:“当代社区的两种空间:地域与社会网络”,《社会》,2008,5:41-57+224-225。
陈友华、佴莉,2016:“社区共同体困境与社区精神重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56(4):54-63+189。
程玉申、周敏,1998:“国外有关城市社区的研究评述”,《社会学研究》,1998,4:56-63。
费孝通,2013:《乡土中国》(修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冯钢,2002:“现代社区何以可能”,《浙江学刊》,2002,2:5-11。
桂勇、黄荣贵,2006:“城市社区:共同体还是‘互不相关的邻里’”,《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36-42。
——,2008:“社区社会资本测量:一项基于经验数据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08,3:122-142+244-245。
郭圣莉,2006:《城市社会重构与新生国家政权建设:建国初期上海国家政权建设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贺霞旭,2019:“空间结构类型与街邻关系: 城市社区整合的空间视角”,《社会》,2019,39(2):85-106。
胡映芳,2017:“公共性再生产:社区共同体困境的消解策略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7,12:96-103。
金耀基,1999:《从传统到现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蓝宇蕴,2017:“社会生活共同体与社区文化建设——以广州幸福社区创建为例”,《学术研究》,2017,12:66-76。
梁漱溟,2005:《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刘建军,2016:“社区中国:通过社区巩固国家治理之基”,《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3(6):73-85。
舒晓虎、陈伟东、罗朋飞,2013:“‘新邻里主义’与新城市社区认同机制——对苏州工业园区构建和谐新邻里关系的调查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13,4:147-152+170。
唐亚林、陈先书,2003:“社区自治:城市社会基层民主的复归与张扬”,《学术界》,2003,6:7-22。
田毅鹏、刘杰,2008:“中西社会结构之“异”与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社会科学》,2008,5:73-77。
吴晓林,2019:“治权统合、服务下沉与选择性参与:改革开放四十年城市社区治理的‘复合结构’”,《中国行政管理》,2019,7:54-61。
熊易寒,2019:“社区共同体何以可能:人格化社会交往的消失与重建”,《南京社会科学》,2019,8:71-76。
燕继荣,2010:“社区治理与社会资本投资——中国社区治理创新的理论解释”,《天津社会科学》,2010,3:59-64。
杨敏,2005:“公民参与、群众参与与社区参与”,《社会》,2005,5:78-95。
——,2007:“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4:137-164+245。
杨笑思,2001:“西方思想中的“个人 —社会”模式及其宗教背景”,《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5:33-40。
简·雅各布斯,2015:《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金衡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马丁·阿尔布劳,2001:《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与社会》,高湘泽、冯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桑德斯,1982:《社区论》,徐震译,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股份有限公司。
Fisher.C.S.,1984. The Urban Experien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Gans,H.J.,1962. The Urban Villager’s: Group and Class in the Life of Italian-America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Stein. M.R.,1960. The Eclipse of commun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 Study on the Nature of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in City Communities
Zhang Xueli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Abstract:The nature of community neighborhood is one of the core themes of urban community research, and it is also the social basi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The research adopts the perspective of actors, based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breadth, depth and freedom of the community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to extract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and analyze the nature of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s in urban communities in China. It reveals the endogenous needs of urban resid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s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s well as its logic and mechanism. The different social capital structure of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the differential sequence of the trust structure and the pursuit of privacy and freedom of life determin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eliteization”, “ageing” and “shallow interaction”.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led community construction should be supplementary relationship of the residents' self-governing socialization mechanism, and should not be full-participation of the community.
Key words: Community Construction;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Freedom
作者简介:张雪霖,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武汉大学科研基金项目“全媒体时代社区应急管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2020YJ029),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②] 社会资本理论,有两个分支,其中一支是以布迪厄和格兰诺威特等为代表的个体式社会资本理论,强调的是以个体为中心的社会关系构建,行动者能够获取和使用的社会资源;另外一支是以帕特南、科尔曼等为代表的社会式社会资本理论,强调的是整体性的以社会为中心的横向社会信任关系的构建。本节使用的“社会资本”的内涵遵从的是前者,即以个体为中心的社会关系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