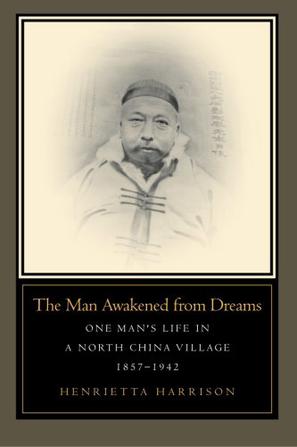- 每隔一段时间,总能看到一些关于“故乡沦陷”、“乡村衰败”的感慨,其中混杂着一种“值得珍惜的某种东西正在丧失”的忧虑和个人情怀,仿佛总与“过去的美好时光”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个问题之所以能激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却正是近三十年来急骤的现代化进程的产物。
现代人其实是没有故乡的。在史无前例的社会变迁与空间流动中,个人的身份是片段的、瞬间的、不固定附着于土地的。人们的生活和土地没有关系,现代人对土地的认同感也因此是相当浅薄的。然而中国文明却又历来是安土重迁的,传统上人们偏好稳固、永久的关系和价值倾向,以此获得心灵上的安宁——“故乡”可说是这一切在空间上的聚集点。与此不同,现代社会是一个通过不断打破原有事物获得进展、极其好动的社会,这首先就表现为眼花缭乱的人口流动,生活中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另一面则是动荡不安,这使人们在获取自我发展机会的同时,往往难以享受精神安宁而陷入一种丧失归属感的困境,因为对他而言,自己成了一个陌生人。在脱离一个共同体的同时,却并没有融入另一个共同体,以至于在两头都产生了一种异乡感。从这种意义上说,“故乡”是在现代被发明出来的。
沈艾娣的《梦醒子》一书以19世纪末山西绅士刘大鹏为例,讨论了中国在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的动荡中,下层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焦虑与折磨。
传统时代自然也有“故乡”,但那并无前述的现代意涵。所谓“莼鲈之思”,是以故乡的名物来衬托个人名利追求的无谓——“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不论是“商人重利轻别离”还是“却望并州是故乡”,在传统的城乡连续体之下,都不存在那种衰败的乡村故土形象,因为那本身就与现代化的结果。到了清末新政推行,城市成为现代化的中心,为此又强化了对乡村的汲取,这才使得城乡二元对立渐渐开始成为一个问题。在当时太原士人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里,已处处可见乡村的萧条。1921年,鲁迅发表了散文《故乡》,自此确立了一个全新的主题——一个离乡又返乡的知识分子眼中看到的、与自己记忆不同的衰败故乡:“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
一个颇具讽刺意味但并不意外的现象是:真正的民间歌谣中,很少有怀乡这一主题,因为那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但在现代城市的流行文化中,它却是相当常见的。1987年,费翔演唱了《故乡的云》,以后的不少歌曲都表现了这类倾向,即故乡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地方(几乎没有哪首歌里唱的“故乡”是城市,更别提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了),并暗示“我”已经疲惫,需要在那里得到安详,那是一个“安宁故土”(peaceful homeland),强调在“故乡”我得到的是心灵上的慰藉,是绝对非物质的。这些歌曲大多十分轻快明朗,如陈明《快乐老家》“有一个地方,它是快乐老家”,它在召唤她“天亮就出发”;韩红的《家乡》说“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牛羊满山坡”——一曲更纯粹的牧歌。郑钧则宣布他要《回到拉萨》,那里“没完没了的姑娘在没完没了地笑”,他邀请大家“来吧来吧,我们一起回拉萨,回到我们阔别已经很久的家”——根据籍贯的常识判断,拉萨显然不能说是西安人郑钧的故乡,但他可以作为自己精神归属。总之,“故乡”是一个快乐平静的、既召唤也期待“我”回归的地方,而“我”也还不需要面对回归后的现实。
与这种“桃花源故乡”不同,另一些流行歌曲也展现了一个有待拯救的故乡,这个衰败的故乡也无一例外位于乡村。1988年发行的《黄土高坡》,劈头第一句就唱:“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似乎着意表现另一种故乡意象,并加上一个光明的尾巴:“我要用辛勤和汗水,把你变成地肥水美……”一年后,《弯弯的月亮》的歌词更耐人寻味:这首歌开头表现的是弯弯的月亮下“童年的阿娇”的情形,似乎非常田园诗意,然而再向前转进却又说现在这月亮有着“弯弯的忧伤”,因为“今天的村庄,还唱着过去的歌谣”——这句有中国特色的歌词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唱过去的歌谣被认为是落后的?
或许可以这么说:在这些流行歌曲中表现了一种矛盾的中国式故乡情结,即故乡从一种意义上说可使人求得心灵慰藉(这需要它最好静止不变),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却又是需要改造的落后之地(静止不变就体现了这种落后)。这两者是有内在联系的一体两面。
刘欢《弯弯的月亮》这首歌的歌词,可说集中了上世纪80年代城乡巨变过程中人们对于“故乡”的纠结心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故乡”的话语是与“传统”相对应的,只不过一个是空间上的“根”,另一个则是时间序列上的“根”。由于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村社的普遍解体,这使个人具有更大的社会流动性的同时,产生了一种无根感,而当他们想要转而去寻求慰藉时,又发现那些已被摧毁。在这种情绪下,人们情不自禁地将故乡发生的变化看作是消极的,虽然如果故乡果真一成不变,他们可能又会愤怒失望,觉得它完全落后于时代。概言之,人们怀有一种不可能满足的愿望,希望故乡既变化又不变,并想要兼得“好的现代化”与“好的传统”,但往往只得到一个好坏兼有的现代化。
对农村故土的乡愁,其意涵也已随着时代发生了变化。在传统上,“故乡”的话语其实常常并不是指一片安静的、没有人的田园画面,相反主要是指一个熟悉的人际关系网络。试回味一下,“荣归故里”、“衣锦还乡”、“造福桑梓”这些词,都暗示着其潜在所指的乃是“父老乡亲”而非一片无人的土地。然而现代的“故乡”话语却是分裂的:它强调一个平静的、田园诗一般的地方,自己可以在那里不受干扰地得到休息,但同时,年轻人对于春节回乡时受到亲友盘问则普遍反感之极,也就是说,他们真正需要的其实是一个摆脱了人际关系的个人主义桃花源。
这种“故乡”话语可说是城市中产阶级内心的投射,由于人们过着一种“工作/休闲”二元分裂的日常生活,与之对应地,就出现了一种心理需要,即在繁忙的操劳之后格外期望能得到平静的心灵休憩。在这里,“故乡”常被置换为类似“家是现代人的城堡”的含义,即一个不可触动的平静之地。很多人离乡原本就是为了去赚钱工作(或委婉地说,“实现自我”),城市被普遍设想为一个不断变动的世界;于是个人的家庭和故乡乃被设置为平静的世界。没有前者的存在,也就不会有后者的意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很多人眼里所看到的“乡村崩溃”或“桃花源故乡”,常常不是乡村本身,而是城市的反面。也正是因此,“乡愁”作为个人内心平静的归宿,如今也被商业化了,对不少旅游胜地而言,“故乡”是一个能唤起游客情感的有用符号。
社会学家魏伟提出,一些移民海外的中国人,往往手持美国或加拿大护照又回中国去做生意,他们中开始流行一种新的话语,即将中国看做冒险家的乐园,而美加是“安宁故乡”(peaceful homeland)。这种话语正表明中国急骤的现代化进程已将这个原本被视为“停滞”的国家全面激活,现在这个重新焕发活力的“少年中国”变成一个蓬勃的、好动的、荷尔蒙过剩的形象,被频繁使用的“热土”、“工地”的隐喻,本身就意味着它不平静——你倒是在一片“热土”和工地上保持内心平静(inner peace)试试!
一动一静谓之道。当中国被视为一个缺乏变化的“停滞的帝国”时,那时的革命者希望它动起来,为此不惜摧毁传统和乡村社会;但当它最终高速运转起来,“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时,现在人们又情不自禁希望能保留一些最后的平静。“故乡”和“传统”因为其渐渐消失,于是成为人们期望留住的对象,而这本身就是现代化进程已趋于深入的标志之一。这一逆向运动最早出现于第一个实现时代化的国家——英国,这实非偶然。日本也是到基本完成现代化的1960年代,才出现重建草根社区运动和传统手工艺的保存计划。用《传统的发明》中的话说,“衰微和复兴令人惊奇地相互混合了,因为往往那些抱怨衰微的人就是带来复兴的人。”
在可预见的未来,城市化进程很难逆转,即便那些抱怨乡村衰败的离乡者,多半也不可能再回到乡村居住——他们身上与城市的联系,也许比他们自己以为的要多得多。农村的变化并不总是积极的,但也不会全然消极,这甚至很可能是它摆脱几百年来过密化陷阱的重要一步——“崩溃”与“衰败”都不是对乡村现状精确的描述,而不如说它是“衰变”,需要注意的只是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劣质化。毕竟,乡村社会的解体,是一个尚在进行的过程,而不是已经确定无疑的结果,何况如果它要重建和再生,这是必然要经历的一步。这并不是说“为了拯救乡村,必先摧毁乡村”,而是要强调这一点:乡村本身并不是外在于现代社会的密闭世界,其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一部分,一个不能变化的“故乡”,最终既不会美好,也不会停止衰败。
- 责任编辑:liudalong
-
- ·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